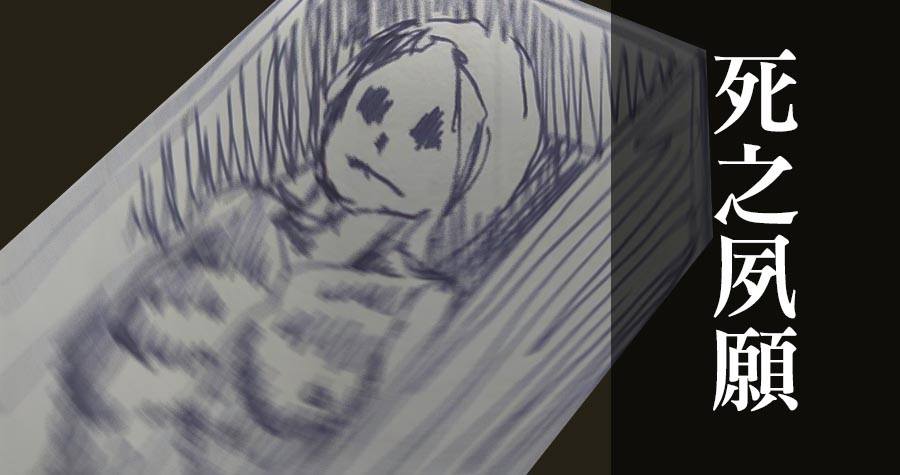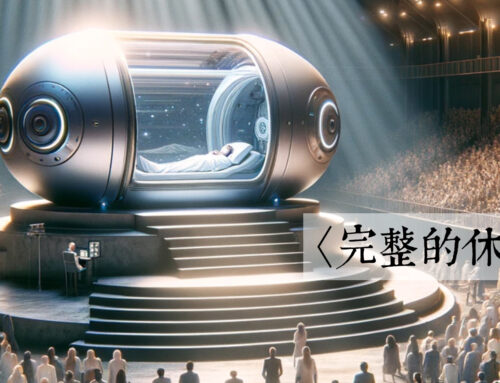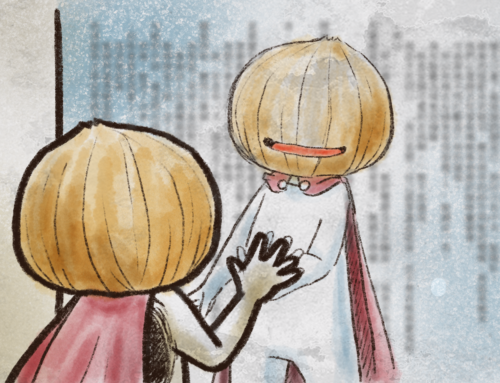我是一個住在望古的禮儀師。
沒有受過任何訓練,只是將屍體透過既定的流程裝入棺材而已。望古這個地方很窮,多數的屍體都是裝在簡單的木板釘成的箱子,再讓他們隨著河流漂走。如果要說這是葬禮,還很勉強,可是我們只能這樣做。
音樂、精心佈置的靈堂、念咒的法師,據聞,踏埠州那邊是這麼做的。習俗上,還要做七個七,滿四十九日後才出殯,中間每七日會有法師團專門唸咒。
我們不一樣。如果人當天死了,我們就會很快地釘起一個簡單的棺材,然後村人會把屍體送到我這裡,整理一下遺容,然後點個蠟燭,傍晚之前屍體就會連同河水,被沖刷到下游。會哭的也只有家屬,有時候連家屬都不會哭。反正在我們的村落,誰病死了也不是什麼大事。
那麼河的盡頭,變成什麼樣了呢?
我常一邊思考這個問題,一邊替亡者整理衣裝。
「你過去之後,告訴我好嗎?」拉整他們衣襟的時候,我會對亡者這麼說著,然後將他們的手交疊在胸前,輕輕的敬拜。「真是抱歉,在你死亡之後,只有像我這樣不入流的禮儀師來為你送別。」
室內經常是一片安靜的,家屬在門外等候,我身邊的燭火也飄渺不定。漫長的時間之中,屍體有各種不同的面貌,但我看見的都一樣是死亡,包括我親近的人死去,也是一樣。秀琴阿姨去世的時候,也是我替她打理的。母親早死,我家已經沒有其他人,將我帶大的是秀琴阿姨。那時候,她被送來的時間慢了很多,或許是因為家中無人,所以沒人發現。整理衣物的時候,我瞥見她稍微腐爛的乳房。失去光澤,顏色也變得青紫青綠,膨脹的幾乎認不出來。
但我還是不禁將臉靠在她的身體上。她的身體已不是記憶中的溫度,很僵硬,表面還有一點軟,像受潮的木桌。我靜靜貼在秀琴阿姨的身上,感受她體內的寂靜。
已經不能再給誰溫暖了。我這樣想著,輕輕地啜泣起來,將阿姨的衣服拉整,順了一下她的頭髮,封上蓋子。我跟村人一起來到河邊,合力將棺盒推到河中,任它漂流。
她就要過去了,那個地方。我從未去過的那個地方,或許就像阿姨死去的胸口,一樣寂靜;棺盒越漂越遠,天色也越來越暗,我聽見阿姨的聲音在對我叫喚。
『離開這個地方。你一定要離開這個地方。』
我驚訝的看著四周,但聲音沒有再傳來;裝著秀琴阿姨身體的棺盒,消失在河的遠處。回去的路上,我順道去了秀琴阿姨家,打開門,看不見桌椅,只有一張床、一個破碗,還有鋁鍋,其他的東西,幾乎沒有。
她沒有剩下什麼在這個村子裡,村人大多沒有。我們的衣裝越來越碎薄,每個人都像是遊魂,大家都快要撐不下去了。這段期間,我還是繼續替大家送行。村人一個一個的去世,我越來越好奇河流的盡頭,到底是什麼地方。於是,在村子裡只剩下我的時候,我下定了決心。
「去看看吧。」我心想。村子裡的人都去世了,我不再需要為誰送行,不需要棺材,因為我是最後一個。
我走到河邊,慢慢地,緩緩地,向著後頭繼續走。深入樹林、日光漸稀,不久,我終於走進一片黑暗。
在那一片黑暗間,我開始迷失方向,像是徒步走進深海,越來越深、越來越黑。不知道過了多久,我開始聽見一些聲音。
我想起來了。
那是我的哭聲、母親的談話聲、還有狂風在吹的聲音。秀琴阿姨說過,母親在我出生後的幾週,就自殺了。這個村子沒有笑聲,我的出生也只是一種不幸,但是,大家都很可憐,沒有誰願意殺死一個新生的嬰孩。
「我是多餘的嗎?」
「沒有人這樣認為。」
十六歲的時候,秀琴阿姨的身體,已經像是五十歲的老人,她躺在屋裡,仍然安慰著我。村人漸漸的少了,到十六年前為止,我是最後一個新生兒,最年輕的我,自幼便開始跟著長輩收拾死去的村人遺體,大家都給我食物,讓我維生。真是受寵。
我是最後一人,他們都在等待離開。這個村子已經完蛋了,他們總說著,等人都死光,我應該要離開。而我也確實等到人都死光後,離開了。
不過,這是哪裡?只有一片黑暗,好像什麼都沒有。我繼續走,一路上,充滿了我從前記得的、不記得的聲音,越來越近。
然後,是大家的雙手。
「對不起,還是讓你來到這裡了。」我停了下來,看著周圍模糊的面孔,心想,我一生見過的每個人,恐怕都在這裡了。
「這裡是望古嗎?」
「是,」一個婆婆走上前來。
「這裡還是望古。」
「而且終於是我們的家了。」
視野逐漸亮了起來,周圍是碧綠的森林,還有那條湍流的河,已透明的不像我印象中,送走亡者的河。看到這裡,我拋開眾人,一路狂奔,一路上,村子的路不再泥濘、景色陌生且熟悉,有些屋子甚至看得見炊煙。
直到我停在住所的門口,粗暴地打開門,看見兩個熟悉的身影回過頭來看著我。
「爸?」
「媽?」我不禁吞了口口水。
「我們回家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