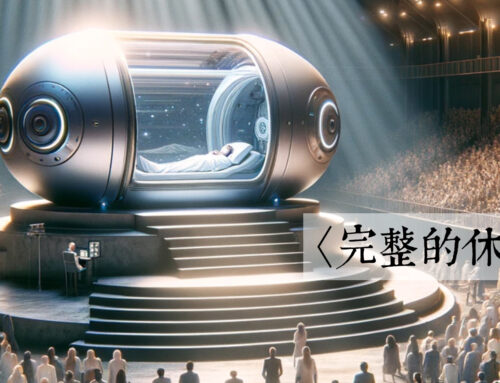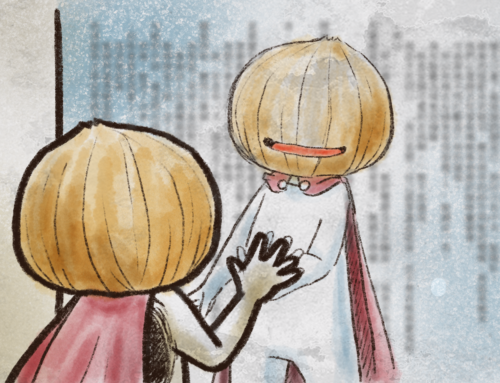這是在筆者開始嘗試將社群網路以文學性為主題推廣時,遇到的一些問題,當然,在問題產生的同時,也順便整理一些想法;因為開始確立一個目標之後,我發現這個圈子在更大程度的事實上,宛若一灘死水。
當然,以下是個人觀點,勢必不能代表整體現況。
但我最有感的是Facebook的贊助廣告。在短期間內的廣告,竟可以不斷推廣到同一批人,如果排除細胞式的受眾計算,推廣的觸擊人數在3天左右才達到1600人次,這無關內容好壞,比較有關係的可能是Facebook給予的推廣觸及有刻意限制,或者經費不足。這還包括AI誤算的、對文學類型內容有興趣的用戶。簡而言之,在Facebook上的廣告結論是,文學類型的受眾很可能是零星分佈的(包括各種社團的活絡程度)。
我原先並不是屬於這個圈子的人,但在試圖進行的時候我第一次有了這麼強烈的感覺:文學被掐住了,它無法擴及一般人。
【文學與大眾的疏離】
這並不是否定文學應有的層次,相對而言,文學應是昇華文化與思想的管道,而非附會在大眾文化下、卻孤獨自持的小羊圈。在臺灣,我們的文化並沒有受到更多文學所帶來的影響,更巨幅的影響永遠是更加視覺性、直覺性的。
視覺性及直覺性無可厚非的成為了現代產品設計的重點項目,我們透過更多的使用者經驗取得了更好的模型,並且設計出精良、簡便的產品,這同時減少了人們在裝置的使用花費更少的時間進行思考。提及此問題,與此同時,出現了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直覺性及視覺性的行為,是否也同時轉移到了使用者的閱讀習慣上面?觀察台灣近20年來的紙本銷量銳減、到數位媒體的內容價值增加(遞減),可以想見改變的不僅僅是閱讀用的媒介,而是閱讀習慣同時改變。
原因或許在於,極高便利性的裝置令使用者加速了閱讀的新陳代謝,但人腦與電腦不同,我們無法像網路爬蟲那樣在一定時間內分析所有資訊,於是我們透過瀏覽的行為對內容價值做大致判定。但這樣的判定選擇長期下來形成了偏誤,多數使用者並非過濾瀏覽資訊價值,而是選擇性的觀看「更輕鬆、易讀」的內容。
這是一個因素,當媒介因素與文化因素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文學與大眾的隔閡也就更加巨大。文學的自限性以及媒介的速食性將內容走向更加推往了兩個極端,在台灣,速食性的資訊在傳播上據有絕對優勢。這是一個警訊,簡易觀察世界從2005~2020年的趨勢,只有少數國家的數位化成功的替國族文化帶來豐碩行銷成果,日本在這一點上面做到了它國無可媲美的結合。俄羅斯則是出現了文化與資本化的強烈衝突,近代,歐美國家更歡迎好萊塢式的電影甚至文學作品,而俄羅斯長久以來仍在對抗這樣的資本主義入侵。
這並非完全是個缺陷,儘管俄羅斯在商業電影上落後美國20年,但他們卻仍保有高度的藝術性及精神娛樂。在《國族精神官能症與大眾文化:類型電影為何沒有在俄羅斯紮根?》一文中提到這一點:
「俄羅斯觀眾是注重故事的人,他們只注意到電影的膚淺敘事——誰殺了誰,誰吻了誰。而且絕對不在意這種謀殺或愛情場景的撥放或拍攝品質。」
顯然,俄羅斯觀眾的想像中,電影理應是一種更具備文學性及敘事性的集成藝術——「藝術」,它具有商業價值,但商業價值是為了所消費的金額能帶來更高的藝術回饋。台灣則是另一種極端的現況,藝文產物難以被明白,變得獨樹一幟,自成一圈。這些圈子在孤立的情況下反其道而行,更將自身定位拱上了過於尊貴的地位,背後因素當然是為了現存利益。於是文學成為了表面上文化主體,實質上卻是整個社會的次文化。它既不視覺也看似複雜,只有文字。在體制中,教育也僅僅將文字作為工具,而非學問看待。
種種複合因素下,文學終於進入羊圈,甚至不經驅趕。其性質使它的發展性更趨狹隘;而羊圈裡的文學要走向商業性,也只有順從圈內的環境,有限的向大眾輸出。這樣的現況牽涉了文學的表現型態、定義,特定明星人物控管了現今文學比賽的潮流,並將其認定為義務,導致羊圈狹隘、難以走出圈外。台灣的「文學」二字並直接令人對唯美、浪漫產生聯想,在新一代的語文學系(含其它寫作者)畢業的作者中,文筆浪漫唯美的作家層出不窮,卻缺乏邏輯性及核心思考;這樣的現象將其歸因,就能從受歡迎的書目中看見「內容零碎」、「共鳴取向」的特徵存在,同時造成寫作者為迎合商業取向,日漸失去主體性。
這樣的類型特徵是符合商業原則的。從前述媒介的視覺化、直覺化,轉變並投射到閱讀的零碎化,最終出現精巧、具備社會共鳴的內容產物已經不是意外。這不能說寫作者素質低落,我們必須要提問:閱聽人怎麼了?
【都是閱聽人的錯嗎?】
綜觀現存的藝文活動,仍然可以見到文學性夾雜其中。在社會主流文化中,城市、愛情元素熱度居高不下,而零碎的字句都具有優美且共鳴人心的特色。這些文句插入在任何一個純文學性質較高的作品中,都仍然能夠順暢閱讀,我們便能從這裡發現極富趣味性的脈絡--現今流行的文學可視為高濃度文學作品的碎片,在媒介的影響下,閱聽人不再如同紙本時代的專注力被分散到了更多廣告、附加內容上。
依脈絡而言,純文學性的內容在關係中理應擔任母體的角色,但這樣的子母關係,卻完全沒有表現在文化主流、次要上,反之,在數位平台開啟了戰爭後,直到2020年為止,台灣閱聽人對於文學性高的作品越加不待見,而通俗作品的文學性雖降至新低點,普遍性卻更為高漲。純文學身為母體的身分,但在大眾文化間卻只是次文化的存在。
但閱聽人仍舊保有對於文學性的嚮往。接下來談到的部分將饒富趣味:當文學性歷經媒介之潮的沖刷,它幾乎只留下一套吸引人的商業模式骨骸,我稱其為「文學靈魂的表面」。這表現在許多文創產業及咖啡廳間。
咖啡與文學,在台灣幾乎成為既定的商業模式,排除其它經營要素,兩者的結合在臺灣觀光地帶、大學周邊已是不可或缺的商業模式;而台灣盛行的文創也與其有關,不同的是,文化創意產業的振興一開始是畸形的,多數商品與產業並非真正融入文化要素,只不過是單純的印刷及再包裝,而「文青」一詞則很快受到喜愛,成為膚淺、光鮮亮麗的代表,一個新的潮流。在《一位德國留學生看見的台灣「假文青」醜態》一文中,提到:
「我不懂的是「文青」到底是怎麼在這個只重數理不重文化的小島上生根發芽的? 一個人怎麼能同時討厭文化歷史、又是個文青呢?而在一個文青數量如此龐大的地方,真正從事文化事業的人又是怎麼一個接著一個餓死的呢?」
該現象是可觀察的。流行文化傳播迅速,在青年間給予的印象鮮明且漂亮,也較為受到歡迎。但文青一詞呈現如此印象並非是因為學文學的族群或讀書的族群層次變得近於一般人,更大的原因在於文青印象的廣泛程度,已使得該詞彙的意義產生質變。因此文青變得更像是風格且流於表象,不再限於喜好文學與藝術的青年族群。
即使在這樣的社會潮流中,我們仍難以見到文學圈致力於突破羊圈的行為。筆者認為,現今文學圈的義務並非「形塑」文學樣貌,而應致力於提升台灣的文學環境,找到台灣文學圈更多的樣貌,讓台灣的文學不再只限於令人詬病的「美文」,讓台灣的文學呈現及品質深入大眾,才是現今最應當思考的作法。文學之珍貴亦有其多元性,能極其唯美、能尖銳刺人的、能夠沉重寫實、能夠趣味橫生,這是文學不可抹滅的特性,而文學也珍貴在這份原始的抒發,若是忽略了這一重點,那麼這個世界,豈不如同失去了大半的文明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