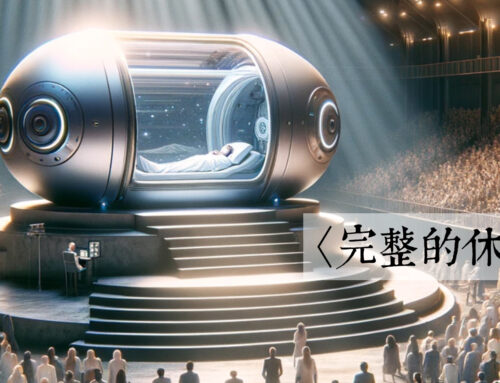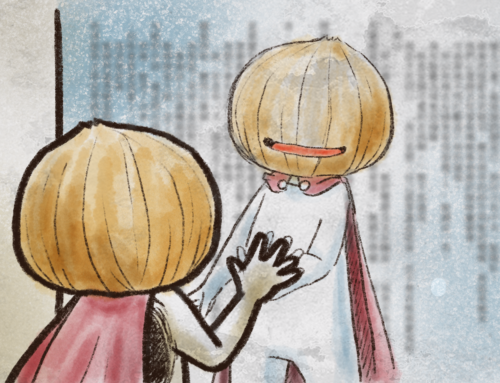「我想告訴你的是,我得到了那把鑰匙,也找到了那扇門。」
C說,聲音聽來像浸泡在黑暗中,朦朧而顯得深邃。一直以來,總在入夜後才會接到C的電話。也許這樣的時刻,才更逼近他內心深處,他真正想說的那些。
你太快找到那個地方了。我說,近乎嘆息。
「是嗎?我以為從這件事來看,時間似乎沒什麼意義,」C的語氣輕盈得很表面,在那之下,永遠有大量的矛盾如悖反的浪翻湧著:「甚至此刻的我是怎麼樣的,或者究竟是不是我,都沒什麼意義,如果這件事本身就是意義的話。何況,我很早以前就找到那扇門了,也許他們反而會說我遲到。」
那此刻的你是怎麼樣的?我問。
「你先說吧?」C反問。
嗯,很累,很沮喪,感覺像沉在沒有光的水裡呼吸。你知道,夜晚對我來說一直都是這樣的,燈光太遠,而黑暗都靠得太近……
「跟你渴望愛與被愛的感覺一樣?」C打斷我。
我們說好不提太困難的事情。我說。輕描淡寫地帶過他的疑問,即使放跑了這樣輕的話語後,身體也稍稍變得沉重:該你說說此刻的你了。我對C說。
「我覺得很安靜。」C回應我,語尾帶著思忖或鄭重的停頓,而後繼續:「不是寂靜無聲的那種安靜,而是所有的東西都在我之外,書本、手錶,穿行的車輛,甚至心跳跟記憶,它們都在我之外的地方,發出各自的聲音。我讓那些聲音一直進來,一直離開,這樣的安靜。你明白嗎?」
大概懂。我說,並反問C:渴望愛與被愛的感覺也是嗎?
我們雙雙陷入沉默,幾乎令我後悔。對我和C而言,這一直是個過於難解的命題。
–
「我想告訴你一個故事,」彷彿是為了溶解這份沉默,C又開口:「關於一個人殺了一個人,得到了鑰匙,卻找不到門,又沒有辦法去殺掉另一個人,只好茫然地活得像個幽靈……這樣的故事如何呢?」
我聽得很認真,但我沒想到C會問我意見:可是你說的這些,關於一個人如何成為另一個人、關於一個人活著卻像在夢裡那樣,偷竊他人的夢境、關於一個人如何把自己活得像一道證明題,求證自己真的是自己……所有這些故事,跟你現在說的這個,有什麼不一樣嗎?
可能我問對問題了。C沉默片刻。可以想像他無焦距的眼神,像在探看自己的樣子。
「沒有吧,」C承認,有點自首的意味:「或許我本來就不該說我不知道的故事,或許因為這樣,我說不出好故事。」
「對不起。」C最後道了歉。
我沒說不好。我安慰他:只要我沒說不好,就不是真的不好。
況且我還挺喜歡的,不論如何變形,總還是有一些什麼無法被抹去的,C的故事。
–
「你喜歡這個世界嗎?喜歡你自己嗎?」C一連拋出兩個問題。對他而言,這兩個問題是合在一起的。
都喜歡。大概就是因為都喜歡,所以才常常覺得很痛苦。我說。
「所以痛苦是好的。」這是C的結論:「雖然我看著還是覺得難受。也許我之後反而有更多機會陪你,我最知道你要什麼,所以我會一直抱著你,直到你忘記呼吸,然後輕輕吻你一下、兩下……怎麼了?不要哭啊。」
好,我不哭。我回答。我想跟C說些故事,但腦海中的文字都在哀戚中飛翔,它們都是詩的模樣。我說不出故事,對此我深感抱歉。
可以告訴我那扇門的樣子嗎?我問C。
「有點難,那太巨大,也太近了,你知道這樣的事物通常是最難描述的……」C的語氣中帶有猶豫。即使委婉地表示了無能為力,卻還是試圖斟酌字句:「但我可以說,跟你想像的差不了多少,只是再無聊一些吧,事情總是這樣。」
嗯。我應聲表示明白。
下次再說故事吧,更多你不知道的故事。我說。
「好。」C很快地答應:「如果還有機會,我想告訴你,關於門後面的那些故事。」
好。我回答他,然後兩個人都沒有掛斷電話,卻在沉默中,兩人幾乎都成為不存在。我們都知道,這樣的沉默將持續到許久以後,一直到他把漫長的門後,說成一個故事。